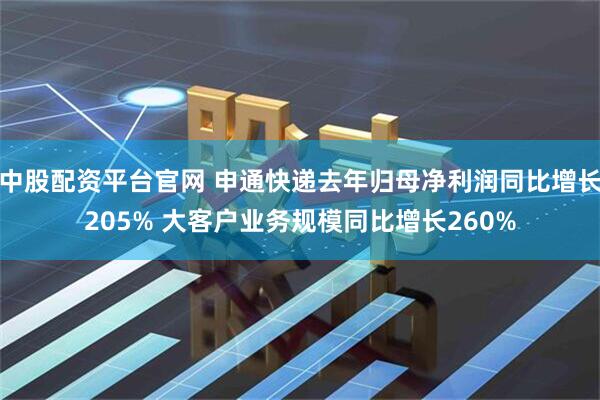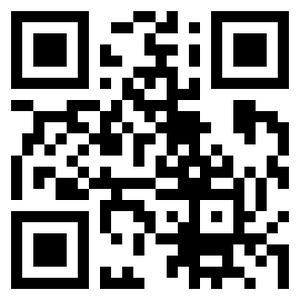次等国家在印太地区秩序转型中的施动性炒股配资平台技巧
图片
作者:金宰永(Jae Young Kim),麦吉尔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候选人。
来源:Jaeyoung Kim, “The Agency of Secondary States in Order Transition in the Indo-Pacific,”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7, No. 1, 2024, pp. 1-29.
导读
随着逆全球化力量的增长、新兴大国的崛起,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和疫情大流行,自由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面临考验。印太地区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前沿,该地区的次等国家日益关注中美竞争造成的地缘政治后果。作者认为,经常被视为“棋子”的次等国家可以通过采取各种战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从而将这种情况转化为己方优势。也就是说,次等国家可以塑造中美战略竞争的面貌和新的印太地区国际秩序。此外,针对现有研究忽视了次等国家可以提升自身施动性这一现实,作者从三个维度解释了施动动机、动员资源的类型、合作伙伴的可用性。这有助于解释小国如何参与重塑印太地区的国际秩序。
引言
文章首先概述了当前印太地区秩序转型的特点,即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正面临着一场复杂的危机,这场危机在破坏其合法性的同时,也扰乱了作为其基础的权力分配。然而,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大国物质能力的再分配,无法合理解释印太地区次等国家的作用。在此背景下,作者意图分析次等国家的施动性,以表明只要有意愿和能力,次等国家就能影响地区秩序转型。
自由国际秩序的危机
自由国际秩序建立在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和多边主义之上。在当前的危机中,自由价值观、制度的消亡与物质能力的重新分配同时发生。全球化的推进产生了逆全球化力量:特朗普的总统任期表明,美国可以通过放弃不再符合其利益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制度,实现利益最大化。人们越来越担心,人类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活动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和大流行病将不断破坏生态系统,但应对这些挑战的集体行动尚未完全实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也改变了传统的权力分配。
作为中美战略竞争的前沿,印太地区秩序的转型尤为引人注目。事实上,印太概念本身就是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产物。随着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启动旨在对抗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印太经济框架”,印太概念正日趋制度化。印太概念旨在将地理范围扩大到印度和印度洋,以此削弱中国在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理论框架
1.秩序转型理论
不同类型的秩序转型理论在以下方面基本达成了共识。首先,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是分层的。这一等级结构的“塔尖”是一个通常被称为霸权或强权的领导国家,它在物质能力方面远超其他国家,同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其次,国家间政治是由大国兴衰所决定的,而大国兴衰是由不同的经济增长率所决定的。当老牌大国的经济增长逐渐放缓时,崛起国就会迎头赶上,挑战前者的主导地位。最后,两个大国之间的大战是改革或取代现有国际秩序的关键路径。如果崛起国对现有秩序下的利益和特权分配不满,战争的风险就会增加。
然而,现有理论在解释印太地区秩序转型上存在三个局限性。首先,它们主要关注的是大国政治中物质能力的再分配和战争爆发。其次,现有文献往往将不稳定和战争爆发归因于崛起国的修正主义,而将霸权国视为维持现状的国家,但事实并非一定如此。崛起国同样可能致力于维持现状,而霸权国也可能倾向于修正主义。最后,由于专注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战略互动,现有的秩序转型理论往往忽视次等国家的作用。次等国家是指国际社会中所有比这两个大国弱小的国家,这些国家往往被描绘成被动和顺从的行为体,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施动性。然而,在建立、维护和改革国际秩序的过程中,次等国家可以发挥远超预期的作用。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霸权国能否持续保证次等国家的自愿支持和参与。
中美战略竞争也为次等国家参与地区秩序转型提供了契机。一是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双方都越来越需要拉拢和动员合作伙伴,至少要让它们保持中立。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弱小的国家,如果能使力量平衡向一方倾斜,也能成为举足轻重的角色。其次,由于现有自由主义准则、规则和机构的合法性正受到质疑,而中美对新兴印太地区秩序的愿景仍在酝酿之中,因此次等国家可以借机宣传自己对地区秩序的构想。
2.施动性的概念
作者将施动性(Agency)定义为一个国家作为社会行为体具备的部署物质和话语资源以实现特定目标的能力,无论是重塑国际秩序还是诱导其他行为体按照其意图行事。发挥施动性不仅是一种旨在实现特定目标的有目的的行动,也是一种受制于规范和制度环境的社会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的施动性只是一种潜能,其发挥施动性的结果仍然是一个经验问题。
作者从三个维度解读次等国家不同类型的施动性:施动动机;动员资源的类型;伙伴国的能力。
首先,国家发挥施动性的动机通常来自于对威胁的感知。在秩序转型时期,次等国家会感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威胁。在许多情况下,次等国家认为威胁来自于崛起国或霸权国,因此它们选择加入后者以平衡和遏制前者,或与前者结盟以取代后者并享受胜利果实。对其他国家而言,主要威胁是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竞争所产生的环境本身。在这种情况下,次等国家会尽量控制和减少不稳定性,避免选边站或过度卷入大国竞争。
其次,一个国家能否发挥给国际秩序带来有意义变化的施动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动员资源的能力。次等国家往往缺乏大国所拥有的物质资源规模,但只要它们能获取对大国具有战略意义的资源,它们就能发挥物质施动性。即使次等国家不能发展物质施动性,它们仍可通过利用国际规范和规则、制度或政治修辞转而发挥话语施动性。
最后,次等国家的施动性取决于它们是否拥有合作伙伴。次等国家大多缺乏军事力量、经济财富或话语权威,无法像大国那样单独采取行动。因此,它们通常会寻找能帮助其实现目标的合作伙伴。如果次等国家不在大国之间选边站队,而是加入彼此间的联盟,就能形成集体施动性;如果次等国家选择与这些大国中的任何一个结盟来加强自己的施动性,则会产生派生施动性。
印太地区次等国家的施动性
随着自由主义价值观和体制的消亡,印太地区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增多。然而,次等国家可以通过采取各种战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从而将这一地缘政治形势转化为自己的优势。为了论证上述理论,作者比较了次等国家对中国、美国以及印太地区秩序转型的单独与集体反应。
图片
图1 印太地区次等国家的施动性
案例一:朝鲜
自冷战爆发以来,朝鲜半岛与台湾海峡一直是亚洲安全的两大热点。最重要的是,冷战时期,美朝之间的敌意导致朝鲜为维护其国家安全进行核武开发活动,每当美朝中的任何一方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单边行动重塑国际秩序时,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就会急剧升温。在美国威胁的驱使下,朝鲜试图利用其核武计划来威慑美国,并重塑对其有利的地区安全秩序,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个体和物质施动性。随着核技术的进步,朝鲜自愿弃核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然而,应该指出的是,美国转向单边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不亚于朝鲜的核冒险主义。美国的单边主义与针对朝鲜的敌对言论强化了朝鲜的威胁感,为其将核武装作为自卫手段提供了借口。朝鲜的核武活动显示了一个小国有能力对霸权国家行使个体和物质施动性。这不仅打破了印太地区的传统军事平衡,也撼动了美国在全球核机制中的领导地位。
案例二:菲律宾
近年来,中菲在南海的领土争端促使菲律宾努力发挥其施动性。阿基诺三世担任总统期间,随着菲律宾国内对阿罗约政府低调的对华姿态日益不满,以及海洋争端的再次爆发,阿基诺转而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阿基诺外交政策中引人注目的是其决定对中国发动“法律战”。法律战是一种以法律为手段实现战略目标的策略,旨在加强自身的合法性以确保战略优势,同时削弱对手的合法性并对其进行制约。由于缺乏单独对抗中国的物质资源,菲律宾选择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启动仲裁程序。在这场法律战中,菲律宾通过提出其法律诉求,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其个体和话语施动性的作用。最终,在美国的支持下,仲裁庭做出了所谓有利于菲律宾的裁决认定。
自阿罗约政府以来,随着总统更迭,菲律宾的战略也在不断转变。这表明,对于菲律宾应如何应对中国,国内各方几乎没有达成共识。与前任不同,杜特尔特并不认同以牺牲中国投资和市场为代价对华强硬。但在卸任之前,杜特尔特又下令暂停与中国在南海进行联合资源勘探的谈判,这为他的继任者小马科斯继续实施强硬政策铺平了道路。
案例三:日本
日本领导人认为,中国崛起是对日本安全和地位的主要挑战。安倍晋三等新保守主义者强烈希望恢复日本的大国地位,并不断强化中国是对手或威胁而非合作对象的观念。
因此,日本正逐渐从对冲转向平衡,这需要强化自卫队能力,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安全合作。不过,在相对衰落的情况下,日本无法单独有效地平衡或遏制中国。此外,从特朗普政府的退出战略可以看出,美国能否维持其海外安全承诺存在不确定性,而澳大利亚、印度等其他合作伙伴的实力也不足以帮助日本确保有利于自身的力量平衡。因此,日本发挥衍生施动性来补充其不断下降的物质能力,同时将其他伙伴国紧紧地团结在自己身边。这体现在日本的国际秩序愿景中,即“自由开放的印太”(FOIP)。FOIP 旨在建立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加强印太地区的互联互通、繁荣、稳定和韧性。在安倍执政期间,美日印澳还复活了传统的四边安全合作机制。这表明小国有能力调动话语战略来吸引强国,从而促进其利益和地位。
案例四:东盟
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剧,次等国家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这两个大国中的任何一个与其他印太国家之间的力量不对称都是巨大的,以至于这些弱小行为体自身无法产生足够的物质力量来制约美国和中国。此外,大多数次等国家往往向这些大国寻求安全保障、经济收益或两者兼而有之。在这种情况下,次等国家似乎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发展出一种将中美两国排除在外的物质和集体施动性。东盟展示了次等国家话语和集体施动性的潜力和局限性。东盟在冷战时期即坚持中立原则,旨在确保东盟成员国的个体和集体自主权不受美国、苏联和中国等大国的影响。随着冷战结束,东盟成员国通过集体制定地区架构的基本原则、规范和规则,提升了自身话语权。例如,它们提倡“东盟中心主义”原则,即东盟成员可以而且应该在地区秩序的建立中发挥主导作用,这已经被各大国广泛接受。然而,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和东盟内部分歧的凸显,东盟的集体和话语施动的空间正在缩小。从外部来看,大国政治正在削弱东盟在地区架构中的核心地位;就内部而言,东盟的集体机构正在受到侵蚀,原因是东盟内部的分歧和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
结论
文章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从威胁感知、资源调动和伙伴可用性三个维度来解读和区分不同类型次等国家的施动性。它有助于解释经常被视为大国“棋子”或代理人的次等国家是如何发挥自身实力的。随着中美实力差距逐渐缩小,以及自由国际秩序的衰弱,印太地区秩序转型为次等国家发展和行使不同类型的施动性提供了动力和机遇。它们可以通过使力量平衡向有利于美国或中国的方向倾斜,或者通过推广价值观、制度和愿景来改革或取代地区秩序,从而彰显本国的影响力。
然而,文章也存在局限性,一是为证明理论适用性,在案例选择上部分夸大了小国作用,如菲律宾之所以能使裁庭做出所谓有利于菲律宾的裁决认定,本质上仍离不开美国的推动,且此举并未对中国的南海影响力造成负面冲击,更遑论迫使中国的南海立场发生变化;二是缺少对施动性结果的观察,即小国施动性究竟能对地区秩序转型发挥多大影响,但作者也声称“一个国家打算实现的结果与实际结果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因为其他国家不会在本国发挥施动性时袖手旁观”,这实质上说明了当前对秩序转型的研究存在客观限制,即观测对象始终处在不断的动态变化中。
词汇积累
Secondary states
次等国家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LIO)
自由国际秩序
Agency
施动性
译者:李航,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国政学人编译员,研究方向为国际安全与大国战略。
校对 | 李美欣 唐一尧
审核 | 李源
排版 | 张安琪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炒股配资平台技巧,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举报。富牛优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