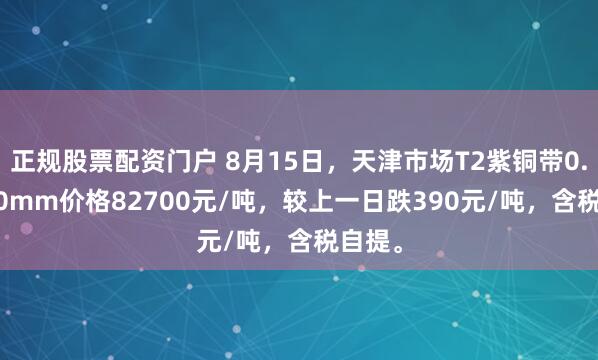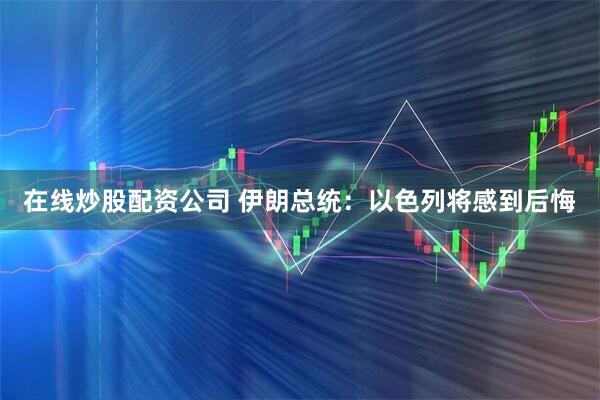图片正规股票配资门户正规股票配资门户
如何发展国际关系理论:来自核心和边缘的启示
图片
作者:Barry Buzan,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名誉教授,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与世界历史。
来源:Barry Buzan, “How and how not to develop IR theory: lessons from core and peripher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8, Vol.11, No.4, pp. 391-414.
导读
本文核心目的在于回答如何弥补以盎格鲁圈为代表的中心地带与外围地带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鸿沟。对于一个国际关系理论而言,何种要素是重要的(What counts)?从分类学的角度来讲,理论是简化的现实,从一种基本的情形出发,各种事件都不是独一无二的,而是共同享有某些极为重要的相似性。这一观点不仅为学术工作者提供了一种基础,也为非学术工作者比如实践家、公共知识分子等提供了框架,使其可以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对于非学术工作者而言,他们的理论体系往往来源于实践,理论宏大且具有总体性,采用“现实—简化—共性”这种模式来提出理论。作者从西方与其他国家在国际关系理论生产方面存在巨大差距这一事实出发,通过比较历史的方法,分别对比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西方(核心)模式与外围(边缘)模式的理论产生动机、理论来源与理论生长的环境。作者在文章中最后提出了对国关理论发展的未来展望,国关理论需要的是将本土的历史与文明财产相结合,产生特色的理论,作者同时也表达了希望以世界历史的视角将整个世界文明体系都纳入整个理论体系的期待。
引言
在国际关系学科知识生产中存在一种分工,其中美国、其它盎格鲁圈国家(Anglosphere)和欧洲的一些地方有国际关系理论,而其他大部分国家没有。因此,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缩小其他国家和西方之间的国际关系理论差距。本文将通过考察国际关系理论兴起的动机、来源和环境以及似乎不利于国际关系理论迭代演进的环境来回应上述核心问题。
本文的有效性基于以下假定:在一个地方和时间形成(或没有)某种行为的事物将与在其他地方和时间产生(或没有)这种行为相关。首先介绍何为国际关系理论,然后通过比较历史的方法分别研究西方(核心)模式和外围模式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最后得出具有指导性的结论。
何为国际关系理论?
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将对国际关系理论采取一个广义的定义。理论是简化现实的。它从这样一个假定出发:在某种相当基本的意义上,每个事件都不是唯一的,而是可以与其他具有重要相似之处的事件聚集在一起。这种观点从分类学出发,同时为学术界的学术意义上的理论和非学术界的大框架思想开辟了空间。在学术领域内,本文在狭义的理论定义上也将遵循上述观点,将更硬和更软的路径都算作理论。本文也同样包含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即某些结构或者实践的哲学倡导,因为其出发点是好的。
本文这种更广泛的方法跨越了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生产者的学术界和实践者的领域。无论是西方还是其他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的思想或世界观,都应该被视为对国际关系的思考,甚至应该被视为国际关系理论,如果它们是强大的、有影响力的、系统的和/或足够概括或易于概括的。
基于上述理解,本文将开始对西方在国际关系理论的成功进行考察。
西方模式(The Western Model,下文亦称核心模式)
欧洲具有从广义理论思考国际关系的悠久历史。现代国际体系以及为人所熟悉的概念(民族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等)和制度大多是在19世纪形成的。在现代国际关系的整个过程中,英国和美国是占主导地位的大国,盎格鲁圈在国际关系理论学术学科知识生产中尤为突出。本文将从两方面讨论其作为知识来源的成功:什么让这些国家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化的丰硕来源以及它们创造国际关系理论依靠的资源是什么?同时,本文也将讨论在结果上,在盎格鲁圈或者更广泛的西方国家中,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是否以及为何存在差异。
在国家性质上,最明显的特征是,英国和美国都是或者曾经是全方位超级大国,其在全球范围内都有经济利益和联系,也是各种广泛的全球网络的中心。较小的盎格鲁圈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新西兰)对国际关系理论也有很大兴趣,这些国家的反常可以用其与上述两大国在文化和学术上的密切关系和互动来解释。这种解释同样适用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作为小国,其在和平研究与安全研究方面富有成效的研究可能同样来源于与美国和英国的密切联系。其次,英国和美国(以及上述的较小盎格鲁圈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是富有的自由民主国家,具有就社会、经济科学和政治问题进行公开辩论的悠久传统。并且这些国家都支持高质量的大学,有鼓励独立研究的强大传统。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一部分,这些大学为理论工作提供了实践、资金和职业激励。独立的学术组织也是重要的促进理论发展的工具。
动机和研究能力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那么什么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来源?首先,西方历史和西方政治理论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来源。几乎可以认定的是,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历史的抽象概念,并与西方政治理论相互交织。例如,现实主义是18世纪欧洲均势和16、17世纪的结合,甚至可以包括古希腊的政治理论。自由主义是从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政府间组织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抽象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对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社会学理论的另一个分支的抽象。英国学派是对19世纪欧洲外交行为的抽象,也是欧洲悠久的法律理论传统的抽象,其基础假设是,包括国际法在内的所有法律都必然以一个社会的存在为前提。建构主义并不是那么明显地从西方实践中抽象出来的,而是从知识哲学中汲取出来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部分伎俩是制造和维持欧洲中心的假定,即西方历史和西方政治理论是世界历史和世界政治理论。只要西方保持全球主导地位,这个神话就相当容易维持。但是,随着非西方国家对现代性的适应,并越来越多地拥有财富、权力和文化自信来维护自己,这个神话开始破裂。
综上,理论发展的一条具体路径是对当前事件带来的压力和激励做出反应。详细来讲,国际关系理论的许多发展受到以下因素的共同作用:拥有全球利益、 全球知识和意识并需要有助于其外交政策的知识的富国和强国;这些国家的教育和公共领域鼓励和允许公开辩论,重视“科学”方法,并奖励学术贡献;在当时流行的一般思想对公众和学术思想家的影响;一系列为国家和社会提供挑战和机遇的各种刺激。由特定事件引发理论发展的一个集中例子是1919年国际联盟成立后,人们对政府间组织的兴趣激增。这构成了所谓的“理想主义”或“乌托邦主义”阶段。上世纪90年代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当时,在冷战结束后为盎格鲁圈创造的良性国际环境下,民主和平论、霸权稳定论和制度主义等自由主义理论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广受欢迎。国际关系理论的来源,或者说受欢迎程度,取决于其与当前事件的契合度,例如现实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兴起。
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三个来源是“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国际关系跨越了许多如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加上世界史,更多通过其所关注的范围来定义自身,而不是某种特定形式的社会行为。由此,国际关系必然是更多地从其他学科引进的,而不像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拥有自己的核心理论或者方法来定义。例如格雷厄姆艾利森引入了组织理论,罗伯特·杰维斯引入了心理学,肯尼思·沃尔兹引入了社会学等。国际关系也同样引进了定量的和后结构主义的方法论。
西方模式内部也存在因文化与制度和本国所面临的外交问题而产生的理论分化。由此,为应对西方中心-边缘体系的边缘地位,欧洲国际关系共同体发展了三种应对策略:学术自立(法国)、顺从的边缘(意大利、西班牙)和多层次研究合作(北欧、荷兰语和德语区)。日本则并不关注理论。欧洲和盎格鲁圈的其他国家也有理论,但与美国的理论存在差异。
从西方模式中可吸取的经验可被总结如下:
大国,尤其是超级大国,更有可能拥有资源和动力来培养对国际关系的思考,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是大学系统资源充足,可以相对自由地追求思想,并拥有促进和奖励研究的激励机制;
至少到目前为止,西方已经非常成功地从自己的历史和政治理论中汲取了国际关系理论,并将其转换为普遍有效的理论;
国际关系作为一个领域的性质使其对来自其他学科的思想和对当前事件作出反应的需要都是开放的。这两方面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源充足、相对自由和开放的大学体系;
文化与外交政策议程的性质和国际关系理论类型的发展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关系。
外围模式(The Periphery Model)
外围地区国际关系思想直到最近才得到相对较少的关注和尊重。与西方相比,外围模式的国际关系思维很少以学术形式出现。本文将采用与研究西方模式相同的方法来研究外围模式。
从国家的性质方面,外围地区在文化、实力和发展水平上是多样化的。在某些重要方面,它们认为自己不仅与核心国家疏离,从属于核心国家,而且对核心国家的统治和种族主义感到不满。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国际关系往往是一个更加强烈和直接的政治主题,往往与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密切相关。这些国家中很少有开放和资源充足的大学,但当国际关系思考更多地是在实践者而不是学术方面时,这一点就不那么重要了。高等教育的管理和资源仍然是核心和外围之间的一个显著差距,尽管,至少在资源方面,随着中国等地的目标是产生世界一流大学,这一差距正在开始缩小。
国际关系理论来源方面,外围国家有一些植根于地方历史和政治理论的外围国际关系理论例子,这是西方模式的主要方法,也是相当成功的欧洲中心论的基础。当其他文化获得现代性的财富和力量时,它们也会希望将自己的历史和政治理论发挥作用。但是,除了中国之外,这种方法还不是外围国家IR理论的主要来源。如印度学者本诺伊·库马尔·萨卡尔(Bennoy Kumar Sarkar)的基于印度古典概念和著作的研究。目前试图在历史和哲学基础上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项目是所谓的中国学派。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关于挖掘中国历史和政治理论,为当代IR理论产生新的概念和见解。它是关于将儒家文化实践与西方假设区分开来,并考察这对思考国际关系的影响。中国也有国际关系的理论化研究,它将自己定位在主流(西方)理论话语中,几乎没有具体的中国差异。
这些发展,尤其是中国的发展,已经很重要了。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它们很可能成为一个更加多元文化和以世界历史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来源。他们可能会加入类似的尝试,挖掘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和知识资源。然而,回顾过去两个世纪的国际关系思想史,其主要动机仍然是对当前事件带来的压力和激励作出反应,特别是以那些被剥削的人的名义,挑战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正统观念和实践,突出的反应例子是依附理论、后殖民理论和泛地区主义。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和对西方统治的普遍不满构成了外围地区国际关系思想的主要共同点,但是这种团结的区域分化也带来了理论的分化。
从外围模式中可吸取的经验可被总结如下:
不应仅仅因为国际关系这一学科及其理论在西方变得更加学术化,就忽视政治领导人和公共知识分子作为理论思想的来源;
对现行秩序的反对可以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动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解决问题”的理论,就像西方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对特定事件和发展的反应一样;
本土历史、文化和政治理论将越来越多地挑战欧洲中心主义。
结论
国关理论发展的三个困境在于资源、干预与竞争。首先,作为外围地带的国家通常缺少相应的资源与激励在大学中鼓励与支持国关理论的研究。其次是资助者的干预,研究经费越来越多地依附于资助者定义的议程。第三是大国竞争,失败方通常会失去成为理论主流的机会。
本文提供了对核心和外围国际关系理论成功的发展以及不利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要素的见解。一个相当明确的结论是,其他国家需要借鉴自己的国际历史和自己的文化和政治理论资源,就像西方和一些外围国家所做的那样,就像“中国学派”现在所做的那样。更全球化的国际关系理论所需要的不是对全球故事的国家版本的竞争,而是对所有国家故事的适当的世界历史综合。
译者评述
巴里·布赞在本文中提供了一个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比较历史视野,系统分析了西方模式与外围模式的国际关系理论来源、发展与经验。在文末,布赞提出了一系列对所谓“中国学派”的未来展望,并且表达了对“中华中心主义”出现的担忧。秦亚青老师在2023年的一篇论文《知识涵化与社会知识再生产——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路径为例》中回应了这种担忧,他指出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目的不是以“中华中心主义”取代西方中心主义,而是向着建构人类共同知识的终极目标迈进。布赞在文中认为以阎学通老师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为代表的理论使用的论据仍然局限于中国古典政治理论,这种认识仍然具有文化上的局限性。关于中国学派的讨论,译者更倾向于支持“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贡献”的说法与秦亚青老师所讨论的双向涵化过程。同时,译者认为,本文在最后回归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特性的讨论而非展示可吸纳的共性,本身就是一种西方中心论的局限。
词汇积累
Periphery
边缘
Anglosphere
盎格鲁圈,英语圈
译者:张倍祯,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兴趣为国际政治理论与国际组织。
校对 | 李源
审核 | 陈扬
排版 | 岳玲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图片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举报。富牛优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